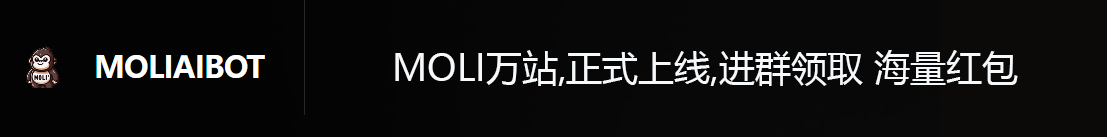CCASH中文网
你的位置:Crypterium中文网 > CCASH中文网 > 追寻量子密宗:物理学家Nick Herbert采访录
追寻量子密宗:物理学家Nick Herbert采访录
- 发布日期:2025-01-04 16:02 点击次数:72 尼克·赫伯特(Nick Herbert):“我相信量子力学只是意识研究的开始,也就是说,它向我们展示了宇宙是如何用极尽绚丽的方式演化出最纯粹的物质。” 我希望智慧真的会随着年龄而增长,一些幸运的人已经证实了这一观点。比如Nike Herbert,他是“Fundamental Fysiks Group”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个由反对主流文化的物理学家组成的团队。从70年代开始,他们挑战“不要说话,只要计算”(shut up and calculate)的风气,并就量子力学领域提出大胆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多奇怪呢?例如:“幽灵般的超距作用”(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1]和印度教佛教的神秘教义有什么共同之处?这种超距作用能够发展成超过光速的交流么?超感知觉是什么?星体投射又是何物?在《嬉皮士拯救物理学》(How the Hippies Saved Physics)这本奇妙的书中,历史学家David Kaiser将如今量子计算和加密的进步追溯到当年Fysiks小组的恶作剧。而现在已经82岁的Herbert就是这本书的关键人物。他在1982年发表的关于超光速通信的论文虽然有缺陷,但是却激发了人们对量子领域的深刻探索。我从未见过Herbert,但是通过读它的博客《量子密宗》(Quantum Tantra),我仿佛和他是非常熟络的朋友。在一篇庆祝博客十周年的文章中,Herbert表示他的目标是“创建一种全新的物理学(量子密宗)”,它将以一种更直接、更亲密的方式把我们与自然连接起来。Herbert的想法有趣、聪慧、甚至带着科学的性感,包含着极大的智慧。我们之间的邮件交流就遵循了他的诗 《量子现实》(Quantum Reality)所表达的含义。———约翰·霍根(John Horgan) 诗文如下: QUANTUM REALITY Shall I look at Her? Or shall I not? Hard Small Separated If I look. Soft Spread-out Connected If I don't. Hard particle and soft wave: both? Small, right-here and spread-out everywhere: both? Lonely separate yet deep connected: both? Honey Some day You gotta show me How You do that. 霍根:你是如何最终成为一名物理学家的呢? 赫伯特:我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一个移民社区长大,那个社区主要有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和斯拉夫人。 我的父母都是在俄亥俄州南部的煤矿小镇长大的,他们在伊利湖旁边的罗雷恩钢铁厂(Lorain steel mill)认识的。他们会说斯洛伐克语和乌克兰语。我的父亲非常聪明,自学成才,虽然高中没有毕业,但是他很会修理汽车、收音机、电视和冰箱,他还是个业余的无线电操作员。 我在学校的时候挺聪明的,我也很想用我的聪明才智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之前我在圣查尔斯波罗密欧天主教预科学校(St. Charles Borromeo Catholic prep school)学习如何当一个牧师,但毕业之后,我选择了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物理,对我而言,相比宗教,物理才是解开谜团更加简单的方式。 霍根:那你又是如何成为一个嬉皮士的呢? 赫伯特:1960年,因为获得了Spunik奖学金,我从俄亥俄州来到了加州。1963年我第一次尝试迷幻药(LSD),那一次,我真正明白了我的无知,我对我所珍视的心灵的力量一无所知。后来,我遇见了我的妻子Betsy Rasumny,她是旧金山的一名舞者,和她一起,我开始探索Haight-Ashbury这个地方[2]。 在帕罗奥图市,我和Ken Kesey一起吸大麻,还和斯坦福的几个人交了朋友,比如Jim Fadiman和Willis Harman。他们正在以科学方式,试验迷幻药的作用。 霍根:这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你从迷幻药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赫伯特:一个人能够经历多少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包括丧失自我)而没有真正的死亡。如果一个人聪明到可以提出正确的问题,这种问题意识比物理学本身更具神秘性。 例如,我曾经非常真切地体验过这样一个事实:“一切都是由思想构成的”。然后迷幻药就失效了。 霍根:是的,我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在你记忆中,Fysiks团队最美好的记忆是什么? 赫伯特: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建造了贝伐特朗支架加速器(Bevatron)之后,Elizabeth Rauscher说:“如果原子是有意识的,那么原子加速器是否有其伦理道德上的意义?” 霍根:你还希望能够创造出比光速还快的交流方式吗? 赫伯特:不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尝试克服这一禁忌来学习一些关于自然的新事物。 霍根:你最喜欢哪一种阐释量子力学的方式? 赫伯特:我哪一个都不喜欢,但祖雷克(Wojciech Hubert Żurek)的退相干机制(decoherence program)似乎最有成效,它产生了更多的新计算。 霍根:量子力学是解释意识的关键吗? 赫伯特:不是的。我相信量子力学只是意识研究的开始,也就是说,它向我们展示了宇宙是如何用极尽绚丽的方式演化出最纯粹的物质。我们应该期待未来以一种更加灿烂的方式来解释心灵的结构,甚至是更有想象力的策略来探索心灵。 对我来说,只有真正爱上自然,才能更好的理解心灵。这就是“量子密宗”的方式。 霍根:你曾经认真对待过超感知觉吗? 现在还会这样吗? 赫伯特:我不觉得自己是什么“灵媒”。 但我的生活中似乎充满了许多不可能的、幸运的巧合,以至于我倾向于相信一些明显的通灵现象(这些现象有充足的文献记录)只不过是其他更深层次精神联系表面的“浮沫”。 你觉得科佩尔蒂诺的圣约瑟夫(St. Joseph of Copertino)[3]怎么样?那个会飞的?如果有像他这样的人出现在帕罗奥图,不是非常适合来做科学研究么? 霍根:我会查查这个人。那么回首过去,你认为量子力学和东方的神秘主义可以类比吗? 赫伯特:多年来,物理学一直被认为是“高中时人人都讨厌的学科”,但卡普拉(Fritjof Capra)的《物理学之道》(Tao of Physics)让这门学科重新变得性感起来,为海兹·帕各斯(Heinz Pagels)的《宇宙密码》(Cosmic Code)和我自己的《量子现实》(Quantum Reality)等量子物理学科普类书籍的畅销铺平了道路。 然而,我很遗憾地说,尽管我深深沉浸在量子悖论中,也沉浸在深刻的思考和绝对的专注之中,但我依然发现它们都非常神秘,几乎没有共同点。 霍根:你相信启迪吗?你有没有遇到过让你印象深刻,能够启发和开导你的的人? 赫伯特:当你遇到一位导师,不过你自己信仰的是什么,你都能非常直接的感受到导师的气场和能量。我见过许多名家,也遇到过很多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会追随这些导师的精神之路。不过最近真正使我感受到极高的精神力量(shaktipat)的是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但是我更多的是感受到他的一种人格魅力,而不是他给我带来了什么“启迪”。 霍根:我们未来能够理解现实吗?还是会走向一条更加奇怪的道路? 赫伯特: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牛顿的观点:“知识的岛屿越广,无知的海洋越大。 霍根:现在你对物理学的看法是什么? 赫伯特:依然是迷雾重重。主要是宇宙学的秘密和太阳系的探索。当然,还有量子力学对现实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霍根:当我采访戴维·伯姆(David Bohm[4])时,他预测未来科学和艺术的界限将会消失。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赫伯特:如果量子密宗真的成功了,毫无疑问,艺术家们将是第一批挖掘这种全新的精神物理学资源的人。 霍根:我赞同你的想法。从你的博客文章来看,你看上去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你的快乐秘诀是什么? 赫伯特:良好的基因。 我的外公外婆几乎不会说英文,从黑钻石(华盛顿州)退休后,他们在俄亥俄州的麦地那(Medina, Ohio)买了一个小奶牛场。从黎明到黄昏,他们在那里养牛、养鸡、种玉米、酿酒。外公在一次矿难之后失去了几个手指,但是他仍然可以挤牛奶。他们是我认识的最幸福的人,他们从不抱怨。 我也不会抱怨。我非常感激自己能够投入全部的精力,和这么多有趣的朋友一起探索生命的奥秘。 虽然我从未真正察觉到,但我怀疑在内心深处,有个小小的声音在低语:无论此刻我觉得生活有多痛苦,它肯定比煤矿里搬石块更让人震撼。 霍根:你理想中的乌托邦是怎么样的? 赫伯特:社会学方面,我一无所知。 我最喜欢的诗人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Shine, dying Republic)对人类进步持悲观态度。也许我们现在正生活在西方衰落之前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无论如何,还有接下来这首诗支持着我,让我在这种复杂之中正确地生活: Love this well ere it perish. And thank you for your mystery which I almost entirely do not understand. 关于作者: 约翰·霍根(John Horgan)是史蒂文斯理工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科学写作中心的负责人。他的著作包括《科学的终结》(The End of Science)和《战争的终结》(The End of War)。 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不代表《科学美国人》。
相关资讯